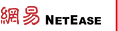殊途(长篇未完)
2007-09-07
A
已经过了立秋,天不那么热了,渐渐地凉下来。
大唐南俨然秋高气爽。
潇湘坐在临湖的位置,看到一只仙鹤斜斜划过水面。
“潇湘姑娘,”苏贺隐端了一杯茶过来,“上次见面时还是在长安,可惜令尊令堂——”
“恩。”潇湘随口答应,看窗外偶尔飞过的仙鹤,心生厌倦。
天色尚明,将暗未暗。
潇湘看到不远处一个买醉的女子,衣着华贵,大口喝酒,满脸麻木。
潇湘第一次喝酒,是在及笄。
说是喝,其实不尽然,不过是以筷子沾了些许剑南烧春,进嘴的瞬间只觉火辣辣的麻。
遇见慕容那年,潇湘不过二八。
那是一场盛大的牡丹花会。在那些绚烂的落花中,潇湘看到一个白衣男子,从此,遗落了芳心。
后来,武才人称王,将牡丹逐出长安。潇湘开始喜欢一种叫虞美人的花。
那是一个秋天,潇湘在万花客栈门前看到大片大片的虞美人,红的象火一样,薄薄的四片花瓣,总觉得好象罂粟。
潇湘看四下无人就偷掐了两朵,把花瓣夹在古旧的《诗经》集子里,夹成干花,到了最后薄如蝉翼,是极淡的紫,好象黄昏后的天。
潇湘想起自己的过去,记忆中却总是有虞美人大片大片的嫣红,没有香味。那样美的花,却没有香味。
B
红蔷很喜欢坐在临湖的位置看偶尔飞过的仙鹤,看它的翅膀掠过水面,一如当年的易水寒。
其实,易水寒看的或许不是那个湖泊而是湖泊后面的金山寺,可这又有什么区别呢。
红蔷喜欢坐在临湖的位置喝剑南烧春,易水寒走前一直在喝的酒。
小二帮红蔷续上第二壶。
红蔷仰头干了一杯,香醇凛冽,不愧为天禄坊所酿,自己如此豪饮只是糟蹋,即便以思念某个人的名义。
红蔷记得自己第一次喝酒,才十三岁。当然,并非剑南烧春之类的佳酿,不过如烧刀子之流的粗陋水酒。
那时为了活计,红蔷在铜官坊当学徒。
很少会有女孩子干这个,大唐南的女孩子,不是去了水碓坊就是进了万花客栈。
红蔷记得,当时陶三彩什么也没说,只是给她一个盆子让她和铜泥。红蔷默默接过来,一声不坑地和,半个月后,坊主陶三彩当了所有陶工的面宣布她成为学徒。
铜泥有种特殊的味道,介于铜臭与煤油的综合,加之和过铜泥的手很难洗净,掌纹中指甲缝间总有些黑色。
和铜泥得反复地揉,中间还要不停地加煤油,一日下来整只手都会脱皮,因为酸痛,手都懒得抬,连拿筷子时手指都是僵的,不,是拿勺子。
红蔷至今还记得那个被摔得粉碎的陶盆,那是她花了3个铜板买的。
刚买的第一天便被人打翻在地,饭菜撒了一地。
那个故意撞她的女孩伸脚在唯一的那块红烧肉上踩了一脚,嘴里说着“好臭”便跑开了。
红蔷蹲下身,看到碗已经完全碎了,顿时心疼得要命。随即捡起那块肉,只略拍了下便放进嘴里,含了好一会才肯咽下。
四周的人对她指指点点吹口哨,突然身后有人大声嚷嚷:“你们别欺负人家新来的!”
红蔷转过身去,她认得他,曾无涯——铜官坊刚出师的学徒。他帮她买了个铁碗,又重新盛了一份饭菜,憨厚地笑:“这样就不怕摔了,吃饱了不想家。”
红蔷13岁那年,遇见曾无涯。
那一瞬间,红蔷的眼泪差点流下来。那么多年,他是第一个跟她提到家的人。
红蔷其实没有家。从前有的,后来就没有了。
因为叔叔起了篡位谋反之心,设计杀害了她的父皇,逼死了她的母后,在逃亡的途中,又生生砍下了她小弟弟的头颅。她东躲西藏,好容易来到大唐,方才得到一时安宁。
在铜官坊当学徒的日子里,曾无涯很照顾红蔷,不知不觉中,她的目光总对着他打转。她是新手,而他总肯耐心指点她。
大唐南因了靠近阳关,秋冬时总是阳光灿烂,不那么冷,却也因此风沙极盛。
铜官坊就红蔷一个女子,多有不便,她跟万花客栈的几个丫鬟一道住。
不那么大的房间里,硬是住了十几个人,地上是密密麻麻的通铺,房间里永远挤得要命,闷热难挡,永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馊味。好象饭菜变质,又好象谁积了一大包脏衣服。
红蔷其实很爱干净,隔不了几天便要去湖边洗头发,她的发质很好,乌黑油亮,好象一匹上好的黑缎子。
同住的几个小丫鬟很羡慕她的头发,老缠着问是哪买的香膏头油,红蔷支吾着说不出话来,问急了只说用的皂角叶子捣碎了的汁擦的。
那天天热,红蔷站在院子中央晾头发,想快些干了好睡觉。
万花客栈的门楼上挂了几盏明亮的大红灯笼,无数的小虫子小飞蛾子围着那些灯笼绕了圈飞,有酒客路过看到她,吹着口哨说:“没想到你披着头发这样好看,比扶摇都好看。”
扶摇是万花客栈最红的舞姬。
红蔷第一次被男人那样称赞,涨红了脸。
曾无涯站在那里,与她说了几句闲话,提起酒坛子海喝了一口,忽然玩笑似地问:“你喝不喝?”
不知为何,红蔷生出一种莫名的勇气,接过曾无涯递过的酒,只喝了一口,就呛得连眼泪都要咳出来似的。
曾无涯哈哈大笑,帮红蔷拍背,热热的手掌隔了她的粗布罗裙,仿佛一块烙铁般,将她的心慢慢融化。
过了不久,曾无涯被坊主分去烧窑。
红蔷渐渐很少见到曾无涯,总是怅然若失。
有次她得了闲,特地跑到曾无涯的住处,老远便听到他的笑。红蔷眼尖,透过半闭的木窗棱看到他和红袖坐在床沿说笑。
红袖是万花客栈的歌女。房中并非没有板凳。
红蔷脸色煞白,在窗外站着,四周的风仆仆地吹到她身上。她只站了一小会,便走开了。
万花客栈的门前种满一种花,红蔷不知道名字,红色的,薄薄的4片花瓣,在阳光下看来是透明的,仿佛呵口气便会化掉。可颜色那样地浓烈,血一般的红,密密麻麻地开着,她心里想,这样的花,为什么一点也不香。
C
长安的宫城种满了高大的广玉兰,枝叶繁茂。
太阳不那么毒辣的日子,潇湘喜欢在这些树下散步。
有一次潇湘随父亲去宫中赴宴,路上一片树叶打着旋落下来,“喀嚓”一声轻响,正好落在潇湘脚边。
这种树叶有大片的硬挺叶面,一面光洁如革,一面有细密的淡黄绒毛,很象枇杷树的叶子。
潇湘突然想起秦府,那时,秦琼在自己家中设了一个书塾,好多宫城中的官员都把自家孩子送去启蒙,一如潇湘的父亲。
书塾在秦府的北偏院,边上种了不少枇杷树。潇湘小时候总爱和一群男孩子去摘枇杷,那些男孩爬上树摘,潇湘在下面不停地捡。其实,枇杷从来不好吃。
宴会设在含元殿,在一边的小花厅刚好遇到幼时的同伴——工部侍郎武士彟的次女——华姑,她是要进宫的。潇湘记得幼时在秦府,她顶顶喜欢捡地枇杷树叶,然后用毛笔写一行行的诗。
宫廷宴会多,当潇湘再次随进宫,华姑拉着她去后花园。
潇湘看到那片叶子上写:“困倚危楼,过尽飞鸿字字愁。”
也许是想起秦府的那段旧时光,潇湘学了阮夫子的样子,摇头晃脑地吟诵:“所谓美人者,以花为貌,以鸟为声,以月为神,以柳为态,以玉为骨,以冰雪为肌,以秋水为姿,以诗词为心,以翰墨为香。”
华姑没有听完,就作势在她手上拍了一记,说:“只有你会这样掉书袋。”
回忆起幼时,其实潇湘与华姑不怎么亲近,彼时在书塾,潇湘颇有些独来独往的意思,加上两家的父亲政见不那么契合,平时见面也不过点头微笑,客气而疏离地寒暄几句而已。
其时,潇湘的父亲有意想为潇湘找个好婆家,于是带着她出席各色宴会。
潇湘恰恰是最烦那些繁文缛节、世家公子的,好在华姑在,两人因此逐渐建立了友谊。
华姑进宫的前一天晚上,特地叫潇湘陪她度过少女时期的最后一个晚上,两个女子挤在一起说了好一阵话。
潇湘向华姑无意提到:“小时侯背《论语》背不出,就装肚子疼。”
华姑想象不出潇湘刻苦背书的样子,小时在秦府,便没见她下过什么工夫。再后来,她已经是誉满长安的才女。
“所谓才女,也不过是沾了父亲的光,如若,我的父亲不过市井小民,才华再卓绝超群,谁来理我?”潇湘的眼角微向上翘,不笑也是笑眯眯的样子,此时却有一种淡淡的冷漠。
华姑隐约察觉,这个女子心底里的寂寞。